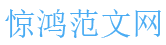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回忆叙述策略,供大家参考。

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的回忆叙述策略 ——On the Remembering Narration Strategy in Kazoo Ishiguro"s The Remains of the Day 作
者:
邓颖玲
作者简介:
邓颖玲,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叙事学研究。
原发信息:
《外国文学研究》(武汉)2016 年第 20164 期 第 67-72 页
内容提要:
《长日留痕》是当代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代表作。小说以日记体形式,叙述了管家史蒂文斯在英国西部进行的六天旅行。回忆既是小说的叙述形式,也是作者结构情节的方式。史蒂文斯对往事的叙述体现了回忆的不可靠性、碎片化和选择性特点。回忆叙述在整个叙事中成为了小说不可或缺的主题,一方面凸显了所选择事件在史蒂文斯心中的地位,使读者看到他终于有勇气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对肯特小姐的爱和对达林顿勋爵趋于客观的评价;另一方面也模糊了不同事件间的界限,使回忆中弥漫着沧桑的历史感,这也是作者石黑一雄本人站在客观角度上对历史进行的一种重新审视。
On the Remembering Narration Strategy in Kazoo Ishiguro"s The Remains of the Day
关
键
词:
石黑一雄/《长日留痕》/回忆叙述/不可靠性/碎片化/选择性/Kazuo Ishiguro/The Remains of the
Day/remembering narration strategy/unreliability/fragmentization/selectivity
期刊名称:
《外国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
2016 年 12 期
《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是当代著名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于 1989 年获英语文学里享有盛誉的“布克奖”。小说以日记体形式,叙述了管家史蒂文斯(Stevens)在英国西部进行的六天旅行。这六天的行程既是史蒂文斯的西部之旅,也是他的回忆之旅和心灵之旅。史蒂文斯一面享受难得的几日清闲,记录着沿途见闻,一面回忆达林顿府邸(Darlington)在战前辉煌一时、战后没落易主的历史命运。回忆是《长日留痕》的主要叙述形式。主人公不仅是在回忆中追述自己的一生,也是在回忆中追寻自己存在的文化记忆、身份记忆,甚至是隐藏在背后的历史记忆。故事在史蒂文斯的回忆中不断绵延、迂回往复,使过去与现在不断交织渗透,完成了小说叙述形式与主题的同步升华。
一、回忆的不可靠叙述
《长日留痕》的情节大致可分为两条线:一是史蒂文斯对其六天出游行程的记录;二是他对战前在达林顿府服务岁月的追忆,这部分占据了全书的主要篇幅。从整部小说来看,回忆既是小说的叙述形式,也是作者结构情节的主要方式。史蒂文斯对往事的叙述体现了回忆叙述的特点,即叙述的不可靠性。
不可靠叙述最早是由叙事理论家韦恩·布斯提出。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布斯对不可靠叙述进行了定义:“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范式(即隐含作者的范式)保持一致时,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Booth 158-159)。很明显,布斯衡量叙述是否可靠的标准是作品的规范(norm),即作品中“人物、文体、语气、技巧等各种成分体现出来的作品的伦理、信念、情感、艺术等各方面的标准”(Booth 73-74)。若叙述者的叙述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保持一致,那么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否则,则不可靠。回忆是《长日留痕》构架小说的主要叙述形式。小说中史蒂文斯对往事的叙述,因以回忆的方式呈现,出现了对历史事实的扭曲和与作品本身标准的背离,造成了不可靠叙述。丽贝卡·卡尼也明确指出“(叙述的)不可靠实际上是石黑一雄小说世界的基底,这一点在他的第三部小说,也是布克文学奖得主《长日留痕》中尤为显现”(Karni 76)。
亨克在论及回忆的特点时指出:“回忆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它与过去所经历的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个人的‘内心故事’是建立在现实的需求之上,并经历持续不断的改写与校订”(Henke 80)。可见,回忆总是迎合当前的需要而对过往事件加以重构。出于意愿的需要,叙述者在回忆时可能有意回避,或有选择地加工重构。而“这种体现回忆扭曲事实能力的精致重构,可以被看作是石黑一雄全部文学作品的主要关注点之一”(
2)。在《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身处“二战”前后的巨大社会变革之中。在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下,其当前的需求便是重新确立自身价值,通过回忆来证明自己是一位“杰出”的男管家。史蒂文斯认为判断一位男
管家是否“杰出”,应当遵循这样的标准:“肯定地讲,一位‘杰出的’男管家只能是这样的人:他能自豪地陈述自己多年的服务经历,而且宣称他曾施展才华为一位伟大的绅士效过力——通过后者,他也曾服务于全人类”(112)。①可见,史蒂文斯是否“杰出”直接依赖于达林顿勋爵是否“伟大”;“只有通过其雇主,史蒂文斯才能建立自身的价值”(Gurewich 78)。因此,在回应战后外界对达林顿具有反犹太倾向的指责时,史蒂文斯有意进行了不符合事实的辩护:“在我为勋爵工作的所有岁月里,我的职员队伍中曾有过许多犹太人,而且我要更进一步说明,他们从未因为其种族之故而受到任何不同的待遇”(139)。然而在试图找出这些“无理指责”的真正来源时,史蒂文斯叙述了 1930 年初达林顿勋爵事实上的反犹太行为:
比如说,我今天仍记得很清楚,在一个晚宴上,席间曾提及某家报纸,我偶然听到勋爵说:“哦,你是说那份犹太人的宣传报刊。”这之后,在那段时间里的另一场合,我记得他交代我停止对当地一家定期来到府上的慈善机构捐款,那是因为该机构的管理委员会“或多或少与犹太人类似”。我迄今对这些话仍记得起,因为它们当时确实让我很吃惊,勋爵在此之前对犹太种族可从未表露过诸如此类的敌对情绪。(140)这里提到的事情与之前史蒂文斯所说显然矛盾,是不实报道,即詹姆斯·费伦所称的“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②史蒂文斯极不愿意承认达林顿勋爵的反犹太事实,因为一旦承认便意味着达林顿勋爵的行为“犹如过去任何的罪恶那般可恶”(143),意味着达林顿勋爵不再是位
“伟大的绅士”,史蒂文斯自己也就不再是位“杰出的管家”。因此,史蒂文斯在叙述达林顿勋爵的反犹太行为时有意淡化,称这些事件“完全属于偶然”、“特别微不足道”。然而,他同时却又说:“我迄今对这些话仍记得起,因为它们当时确实让我很吃惊”(140)。在史蒂文斯充满矛盾的叙述背后,是其内心的挣扎与不安。虽然“史蒂文斯知道历史会如何评判达林顿勋爵,但他又无法让自己承认这一事实”(Wong 61)。因此,史蒂文斯一方面因要回应外界对勋爵的指责,不得不道出事实;另一方面又只能遮遮掩掩以维护勋爵,更是维护自己。通过回忆的不可靠叙述策略,史蒂文斯在重构事件时便有了回旋的余地,他先断言达林顿府上的犹太雇员从未受到过不公正待遇,再逐步淡化达林顿勋爵反犹太的事实,从而树立起达林顿勋爵作为伟大绅士以及他本人作为杰出管家的文本形象。
回忆叙述中的叙述者,因回忆本身的解释性表征以及模糊性,也往往对事实进行不实报道或者不充分报道。在描绘府内职员为 1923 年那次国际会议进行准备时,史蒂文斯曾叙述道:“至于肯顿小姐,我似乎记得那些日子沉沉的重压对她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75)。文中“似乎”二字将回忆的模糊性前景化,且与“显而易见”形成矛盾。当时,史蒂文斯提醒肯顿小姐准备好供楼上使用的亚麻床单。而此刻忙得不可开交的肯顿小姐抱怨道:“史蒂文斯先生,在过去的两天之中,这算是第四次还是第五次您觉得确有这种必要”(76)。由此可见,肯顿小姐受到的如此“沉沉重压”并非事实,而是史蒂文斯自身心理状态的投射,是由史蒂文斯回忆的模糊性引起的不可靠叙述。因为在史蒂文斯心中,杰出的管家应当时刻带
着职业的面具,“他们绝不为外部事件所动摇,不论那外部事件是多么让人兴奋,使人惊恐,或是令人烦恼”(39)。所以,他的叙述一直保持着矜持而客观的口吻,回避任何情感的流露。他“只有在谈论别人时才能谈论自己,而一旦直接谈及自己他便不得不说谎”(Shaffer 80-81)。通过回忆的模糊性而造成的不可靠叙述,史蒂文斯将自己的情绪投射到他人身上,这使读者可以窥见一直戴着“非人”面具的他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他不能直接面对自己的内心情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混乱和精神、心灵的残缺不全。由此可见,不可靠叙述作为作者的一种叙述技巧,它不再仅仅是作为形式而存在,而是已参与到小说的主题建构之中。
二、回忆的碎片化叙述
回忆,是对过往具体事件进行的艺术重组,正如斯蒂芬·欧文所说:“回忆本身就是来自过去的断裂的碎片”。③回忆作为一种意识行为和情感体验方式,运用到文学创作中,不仅是叙事方式和主题呈现手段,而且具有了丰厚的文学内涵和审美意义。在《长日留痕》中,管家零散、深沉而缓慢的回忆碎片与现实生活交叉相融,构建起整部小说的叙事框架,形成了《长日留痕》独有的片段美学。
众所周知,储存在人脑中的记忆并非流畅的、不可割裂的信息流,而是一系列可随意识自由调节的片断。长久占据回忆中心的往往是印象深刻的细部记忆,而且大多是以与其他事实连续不上的片断式呈现。这些记忆碎片往往因外界事物的触发而被唤醒,再通过心理刺激点彼此连接起来,因此,它在小说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史蒂文斯承
担了热奈特所说的“指挥功能”,通过对回忆事件的选择和过滤,对文本和读者进行操控,从而达到他叙述的真实目的。他经常通过这样的表达来进行回忆的选择,如“这整个事件不由得使我想起……”、“回想起那位常使人恼怒的女仆……”、“我怎么也无法忘记那一次……”(47)“我至今仍记得”、“据我的回忆”、“据回忆”(202)等。他甚至在同一段或同一页文本长度内对回忆事件进行高密度、高频率的切换,使文本呈现出碎片化、跳跃性特征。在小说中,史蒂文斯追忆了父亲早年间在达林顿府服务时摔倒的事件。引起这段回忆的源头是肯顿小姐信中对某个场景的描述“倘若这是令人伤感的回忆,那就请原谅我。可是,我怎么也无法忘记那一次我们俩注视着你的父亲在凉亭前徘徊着,目光紧盯着地上,似乎希望找到他丢在那儿的珠宝”(47-48)。这段场景发生在他父亲跌倒之后。因史蒂文斯的父亲在服务时跌倒,达林顿勋爵担心他在两星期后的国际会议上再次出现纰漏,遂让史蒂文斯找其父亲谈话并缩减其工作。然而史蒂文斯并未直接进入这段回忆,相反,他先叙述了肯顿小姐将鲜花送到配膳室的情景,再转到两周后肯顿小姐对其父亲的工作失误不断抱怨,接着跳跃到两个月之后达林顿勋爵找其谈话以及之后史蒂文斯与父亲的对话,再跳回到与达林顿勋爵谈话之前一周父亲摔倒的情景。直到最后,史蒂文斯才用自己的口吻,描绘了肯顿小姐信中父亲“寻找失去珍宝”的情景。围绕着父亲的跌倒,回忆的碎片被组织起来,然而事件与事件之间却留有长短不一的时间空白,回忆的时间顺序也被打乱。这种迂回、跳跃的叙事手法不同于平铺直叙,既体现了回忆本身的场景依存性,也反映了史蒂文斯内
心的挣扎。父亲是史蒂文斯心目中具有“尊严”的“杰出管家”的代表,他曾说:“我希望你会认可,我父亲本人不仅显示尊严,而且他本身几乎就是海斯协会称之为‘与其地位相称的尊严’的典范”(39)。然而随着年龄增大,父亲已经不能胜任管家的工作。父亲的跌倒无疑是一直崇拜父亲的史蒂文斯不愿面对的记忆。然而,父亲被免去一些工作的重要原因,是不久之后达林顿府将召开重要的国际会议,而史蒂文斯则将这次会议视作其职业生涯引以为傲的转折点,是史蒂文斯极想叙述的一段回忆。挣扎在说与不说之间,史蒂文斯便选择了绕开平铺直叙,采用碎片化的、跳跃迂回的方式呈现这段荣辱参半的记忆,以淡化和模糊父亲的年老和失误、突显父亲“杰出管家”的文本形象。
三、回忆的选择性叙述
人的一生当中会经历无数个或远或近的生活事件,但能够明确记起的却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回忆不是被动无情地对一系列资料片段加以储存和提取,而是根据需求,在已被注意和理解的信息中挑选出对自己有用、有利、有价值的信息储存在大脑中,其余信息则往往被遗忘或留在潜意识里。巴特莱特认为“回忆并非无数固定的、毫无生气的和零星的痕迹的重新兴奋。它是一种意向的重建或构念。这种重建或构念与我们的态度有关,与突出的细节有关”(巴特莱特 279)。因此,能够满足需求的信息,记忆程度一般较高,往往成为人们重构记忆的主要信息来源。在以回忆为主要叙述方式的《长日留痕》中,作者或叙事者对人物和事件的选择与过滤同样反映出作者的审美需求。
在《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以回忆的形式,追述了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包括他的雇主与纳粹集团的牵扯、他与父亲僵硬的关系以及他对同事肯顿小姐压抑的感情。他一生痴迷于追求“尊严”,崇拜名誉,把自己最美好的三十五年岁月无怨无悔地奉献给了雇主。他对职业尊严和成就的追求使他时时刻刻保持克制矜持的叙述者形象,回避任何情感的流露。这一点从他作为叙述者所选用的非常正式的语言中可见一斑。他使用的语言语法完全正确,词汇简单精确,表达逻辑严密,一如“管家式的语言,没有任何文学特点,缺少妙语、美感和创意”(Parkes 31)。也正是这种“管家式的语言”,建立了他克制、拘谨、容忍的文本形象。初读文本,读者对史蒂文斯的印象多为冷漠、麻木、不通情理,但仔细分析叙述者对过往事件的选择性叙述,读者会发现掩藏在表层文本下面的史蒂文斯其实有着一颗敏感、细腻、温柔的心。
从元故事叙述层来讲,史蒂文斯作为叙述者,反复实施了...
推荐访问:叙述 策略 回忆 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的回忆叙述策略